2016年9月25日,由中华书局与人文考古书店共同主办的“青钱万选:阅读历史——霍宏伟《古钱极品》首发恳谈会”在北京人文考古书店会议室举行。新书作者、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霍宏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中华书局总编辑助理张继海、编辑杜清雨,中国文物报社新媒体部副主任王超等作为嘉宾出席,他们一起探讨了钱币、考古及学术研究等方面的问题,并与现场听众进行了对话与交流。

恳谈会现场,从左至右为:王超、霍宏伟、许宏、张继海、杜清雨(赵囡囡 摄)
既要钻进钱眼儿辨真伪,又要跳出钱眼儿看历史
讲座伊始,霍宏伟先讲了一段钻钱眼儿的逸闻。有一次,他在家里的大门猫眼上贴了一枚半两钱图片,从门外面一看,猫眼变成了钱眼。有一位亲戚来了说:“你研究钱币的,至纯天珠,可真是钻到钱眼里啦!”其实研究钱币有点像练习书法,必须先入帖,再出帖。只是钻进钱眼儿里可不行,还要跳出钱眼儿来看历史。
接着,霍宏伟又给大家分享了三个跟钱币有关的小故事。
第一个是鉴定南宋钱牌的趣事。霍宏伟说:“我的一位同事的朋友给他发来两张钱币照片,请其鉴定。这位同事本来想找我看看,但是我恰好去图书馆了。之前,我送给他的《古钱极品》这本书在桌子上放着,他便对照着照片翻看,在该书第213页,图30-2这两幅图与其需要鉴定的钱牌相仿,但从形制、钱文、锈色及质地等几方面来看,这枚钱牌是伪品无疑。所以,这位夏商周考古专业出身的同事就很从容地断定这枚南宋钱牌是仿品。当同事讲完这件事情之后,我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本书刚一出版就发挥了它的作用。”
南宋“临安府行用”钱牌伪品与浙江省博物馆藏真品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唐代的咸通玄宝。这种钱是唐代货币中的凤毛麟角,因为李唐王朝币制基本稳定,通行的大部分都是开元通宝钱,很少有稀奇古怪的钱币,所以咸通玄宝就显得有点另类。
2011年,霍宏伟受《中国钱币》编辑部的约请,在该刊开设专栏“国博藏泉”,发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咸通玄宝考》一文。一位东北的读者看到此文后,给霍宏伟写信,文中介绍自己是一位70多岁的钱币爱好者,收藏有不少我国古代的珍稀钱币,若霍宏伟的研究有所需要,可以无偿提供。最让霍宏伟感动的是,他在寄来的牛皮纸信封里还附上了一枚铜钱,正是咸通玄宝,说赠送于霍宏伟搞研究之用。霍宏伟将其与国博所藏的真品图片比对,发现他寄来的那枚是伪品,因为从形制、钱文、锈色等方面来看,其与国博收藏流传有绪的传世品有较大差别。
国博馆藏的咸通玄宝都是民国时期大家们的旧藏。下图左侧这枚钱就是沈子槎先生的藏品,右侧的是罗伯昭先生的藏品,后来都捐赠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经过许多钱币收藏家的鉴定,认为是真品,同时还有其他佐证。


国博藏沈子槎(上)与罗伯昭捐赠的咸通玄宝(下)
需要什么佐证呢?这就要依靠考古发掘品或出土品。霍宏伟把古钱分为三类:考古发掘品、出土品以及传世品。除了国博馆藏的这两枚咸通玄宝传世品外,四川成都还发现一枚咸通玄宝出土品。


成都新都县新繁镇钱币窖藏出土咸通玄宝
1989年,成都新都县新繁镇因为商场施工,在挖地基时发现一处钱币窖藏,重约340公斤,共计出土了62604枚铜钱。2003年,成都博物馆钱币专家曾咏霞女士对该窖藏钱币做了进一步整理,拣选出这枚咸通玄宝。虽然它有明确的出土时间和地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属于正规的科学考古发掘品,仅属于第二类——出土品。根据这枚出土品来看,咸通玄宝的上部及左右两侧外郭略宽,但是其外郭下部变得特别狭窄。以此来比对国博的两枚传世品,其形制特点也是如此。所以,在与发现时间、地点明确的出土品对比之后,我们据此认为国博所藏的这两枚咸通玄宝确实为真品。对照老先生送霍宏伟的那枚咸通玄宝,它的外郭非常均匀,宽窄一致,钱文风格也与真品不同,而且锈色很假,就是看上去很扎眼的那种新绿,故判定其是伪品,当然在老先生的眼中它就是真品。后来,霍宏伟委婉地给他打了个电话:“珍稀古钱不是轻易就能在市面上买到的,建议您以后不要在市场上购买这类稀有古钱了。”
第三个故事是有关国博馆藏新莽时期的国宝金匮直万,像这类古钱前些年还有拍卖行进行过拍卖。民间的国宝金匮直万,恐怕真品极少。
国博珍藏的这枚国宝金匮,称为“完整品”。为什么叫完整品?因为此钱正面钱文读为“国宝金匮直万”,加起来共计六个字。它的钱文清晰,笔画没有损伤,所以称为“完整品”。另外一枚是残缺品,它的钱文“直”字下方横画与“万”字草字头竖画,笔画残缺不全,故称为“残缺品”。

国宝金匮直万完整品、残缺品及拓本
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国宝金匮罕见于世,稀缺到世界上只有两枚半,一枚是完整品,另一枚是残缺品,剩下半个就是《古泉汇》一书中著录的这半个钱摹本,下面的方形缺失,仅残存上面的圆形方孔。从其四字钱文笔画结构、书法风格来看,应是伪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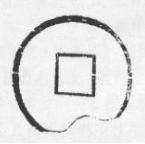
《古泉汇》著录的国宝金匮残品摹本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